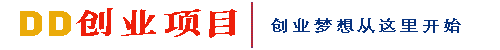大厂中年人:重复劳动、缺乏成就感做无意义、没价值的事
行业盛行加班,产品更新换代,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、更新专业储备等,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。
2022年3月末,38岁的前程序员、财经博主杨曦发现自己“火了”。他最新发布的一条短视频,两三天的浏览量就达到79万。初涉短视频创作一个多月,这让杨曦既兴奋又紧张。
视频中,杨曦的脸撑满屏幕,像是一张放大了的二寸证件照,背光,身后是家中阳台一角,镜头还晃来晃去,他认为把自己“拍丑了”。但互联网大厂、35岁、程序员、裁员等字眼,还是吸引2万余人点赞。一些人评论,“真实”“接地气”;还有人留言,“脸色不正常,近期做过全身体检吗?”
作为互联网大厂的中年程序员,杨曦们自带“流量”,他们服务于快速迭代的互联网行业,与公司一起追求技术创新和财富增长,但中年危机似乎也来得更早。
最初,杨曦被经理告知合作团队对他有所不满,希望他转岗,他自认热爱工作,拒绝转岗。在拉扯中,裁员补偿提上日程,几次沟通之后,杨曦拿到“N+一个月休假+半个月奖金”的补偿。略有遗憾的是,杨曦750股股票期权未到期,只能作废,另一部分股票出售后收获50多万元。
八年前,杨曦从一家二线互联网企业跳入互联网大厂,当时这家大厂以技术强闻名,杨曦跳槽后薪水涨了50%。但时年30岁的杨曦明白,程序员在大厂如果做不到管理层,“35岁后会很被动”。杨曦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在前一家公司,他转过产品经理岗,这是很多程序员工作几年后转型的一个方向,但他自认为做产品经理并不适合,又重回研发一线。
虽是资深程序员,但为避免“35岁危机”及中年之后“路越走越窄”,杨曦在五年前开始积极布局。入职大厂后,正赶上O2O风潮,杨曦在公司旗下团购平台做研发,链接商家和消费者。一年多后,公司战略调整,不再重点发力这项业务,团队大规模削减。
杨曦选择继续留守,即便当年涨薪幅度和年终奖都“特别少”,但他坚信,这个领域将大有可为,因为对中小微商家来说,O2O更容易形成商业生态。杨曦有给一些商家赋能的想法,还请做支付功能的朋友收集不少中小商家的“痛点”,希望开发让商家线上开店的系统,使每个商家都能成为O2O主人。杨曦将思路分享给经理后,获得的实际支持有限。不过经理告诉他,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将部分创新想法提交为公司的创新项目。
杨曦希望这个项目能做成,工作之余,经常加班到凌晨2点成就感做无意义、没价值的事。持续了一年多后,开发的系统实现了杨曦的部分设想,他还自己打印宣传页到自家附近门店推广。但后来杨曦所在的整个业务线收缩严重,最终他的项目“不了了之”,不得不尝试转型其他业务。
当时,杨曦的积极性并未受到太大打击,他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个筛选和预测基金涨跌的小程序。杨曦在上一家公司做过股票和基金方面的后端开发,多年以来爱好买基金,并赚到一些钱。2017年,他发现买入的基金不好,就写代码抓取数据进行分析,在此基础上再买入的基金表现都不错。
利用2018年春节假期,杨曦花六天时间开发了一个基金方面的小程序。在2020年,这个小程序开始商业化,实行会员收费模式,每月3元。“就这么便宜,我当时一个月能卖1000多元。”杨曦说。
不只是琢磨代码,杨曦从2017年开始,利用上下班时间跑起滴滴。他的住处和上班地都是程序员聚集的区域,接单非常快。“下班更好拉,公司那边晚上打不到车,一般取车的时候打开网约车软件,立马就有人回应。顺风车没有关停时,可以选择95%顺路,他就跟你回家路线基本一样。”跑滴滴只是顺路赚点零花钱,杨曦会借此和搭车的同行们交流,了解各个公司的业务,聊聊行业八卦、基金、股票、投资、买房等。
工作这些年,杨曦早在北京买房置业。十几年前,杨曦在通州买下第一套房,当时房价每平方米5000余元,他用炒股、买基金赚来的钱付了首付。2016年,他在通州的房子每平方米涨到2万多元,考虑到换房算二套房的成本,以及从投资角度出发,他卖房后在目前居住的小区先后买了两套商住房。2018年,偶然发现民宿的需求量很大,收益不错,杨曦将房子改做民宿。2020年,杨曦在密云区古北水镇附近又买了一套民用住房,专门托管给中介做民宿。
回顾这些年的多手准备,杨曦表示,他工资部分结余并不多,大部分收入其实来自投资和副业,家庭收入一度主要依赖他一个人。
最初从事的业务收缩后,杨曦转入一项新业务。杨曦称,做了一段时期后,那项业务开始有收入,他记得大约有3000万元,自己还挺有信心。但一年多后,因盈利不及公司预期,整个项目被砍掉,不少同事都不理解,杨曦也一样,他形容这就像猴子掰玉米,吃了一半,看到更好的就把原来的扔掉。
再后来,杨曦转入公司的金融研发业务,此后压力倍增,经常加班,有时甚至通宵工作。杨曦一般夜里10点半以后下班,这算是所在团队走得较早的人之一,晚上10点半去男卫生间,“还经常没有位置”。
累归累,杨曦表示自己其实喜欢做金融方向的研发,这和他在上一家企业的工作经历有关。但他认为公司的金融业务缺乏创新,“做的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,同行可能几年前就做过了。”他对产品开发提出过一些想法,但公司分工太细,有些领导认为技术就应该专注技术,不要“瞎折腾”。而技术方面,他认为多是偏基础的活儿,太简单,重复性强,工作越来越没兴奋感,“纯粹是一份搬砖的体力活”,这是他觉得累的主要原因。
这种重复劳动、缺乏成就感带来的累,38岁的李铭亦深有体会。李铭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“你在做无意义、没价值的事情时,就会累。”
李铭今年离开此前服务近十年的一家互联网大厂,入职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公司,并从技术总监转型为产品运营。
李铭当年刚开始工作时曾憧憬,程序员会朝某个技术方向深入钻研,成为领域内的“大牛”。但随着年资增长,他发现工作中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李铭认为,很多互联网公司偏应用型和产品主导,技术人员主要是执行公司决策。一些公司更希望快速盈利,并不需要程序员有太高深的技术创新。另外,公司用户增长,系统容量提升时,对程序员技术的挑战比较大,当业务稳定后,技术提升的空间有限。因此,李铭认为自己在技术路线上升空间不大时,主动选择转型。
40岁的陈明是一名技术架构师,热爱研发,过去的十几年,他跳槽了七八次,从事过银行和海关相关业务研发,后来转向移动支付领域,目前在一家合资企业从事企业软件研发。
陈明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很多程序员,尤其是资深程序员希望高质量研发,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希望快速做出产品,短时间做出一个产品,先抢占市场,再通过上线新功能来完善,而一旦产品不成功,“大不了就去换新的产品方向”。
作为研发人员,陈明也经历过公司不断试错、产品快速迭代的时期。陈明在上一家公司曾做过助贷业务,这项业务在国内有了起色后,希望开拓海外市场。陈明等研发人员认为,因商业模式和功能类似,公司可以尝试构建一套系统复用到海外。但产品部门不同意,最后在海外市场的每个国家,公司都会重新招聘团队,重做类似的项目。
所幸,海外市场发展比较顺利。陈明称,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很快,产品部门希望赶快出产品,因为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,不可能先去强调系统质量,只能快速把产品推出去,先占领市场,再求发展。“也许他们是对的,很多产品因为市场原因放弃,当业务都没了,东西即使设计得再好再通用,能留下的价值有多少?”陈明提出他的疑惑。
在公司或者社交群里,对年龄稍大的程序员,李铭经常听到大家私下调侃,“你该去滴滴报到(跑车)了,你该去美团报到(送外卖)了。”
虽是玩笑话,但李铭、杨曦、陈明都多少感到尴尬。35岁前后,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,不可能经常像刚毕业的年轻人那样,忍受高强度加班,此外,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也已不如年轻人。资深程序员可能代码写得更精炼,经验更丰富,但薪资待遇已经高出年轻程序员不少,面对一般的基础性岗位,他们的可替代性很大。
李铭打比方说,“就像我们建房,如果盖茅草房就行,就能把钱赚了,你肯定不会找有盖精品大厦资历和经验的工匠。”这几年他负责团队招聘时,虽然不会特意看重应聘者的年龄,但面对竞争力同等或近似的人,他会优先选择年轻人。
百森智投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涛,曾担任过华为全球招聘负责人,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从职业成长规律看,确实存在25岁、35岁、45岁现象:一般情况下,25岁是思考适合干什么、喜欢干什么的阶段;35岁时,则需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。在互联网企业,35岁的理想状态是做到中层,分管一块业务或者产品;35岁之后容易进入迷茫期,中层到高层的通道窄了很多,晋升不上去就会很尴尬。因此,35岁-45岁对职场人最大的挑战是,“我有没有可能冲到VP(副总)层面,在行业领域成为有点名气的人”,如果没有这个机会,内部晋升受阻和外部行业建立影响困难,就会压力倍增。
冉涛认为,35岁对研发人员来说是一个更明显的拐点。互联网行业变化快速,到了35岁,如果积累的技术价值没有上去,实际的能力水平没有超越薪酬上涨,“看起来投入产出比低,胜任度不够,就进入危险期了,但这时候你的家庭支出和消费各方面上去了,降不下来,压力就会非常大”。
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,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字劳动、数字经济与生产等。她曾经出版《依码为梦: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》。
夏冰青表示,她的田野调查贯穿了2009年-2011年以及2015年的互联网行业。早在2009年她开始调研时,当时的第一代互联网员工就向她强调,这是一个青春行业,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退休生活,甚至无法想象自己40岁以后的生活。她认为,这其中的缘由不乏这个行业盛行加班,产品更新换代,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、更新专业储备等,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。因此,所谓的“中年危机”,其实在“初代大厂员工”中就已经达成共识。
近年“35岁危机”的说法进入大众视野,在夏冰青看来,是因为这一现象也在其他行业出现。比如,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体系招聘也或明或暗拒绝35岁以上的应聘者,“互联网行业只是更被人关注”。
拥有十余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的陈方,曾在知名企业和互联网大厂任职。她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35岁在招聘时并不是绝对的限制条件,但不同业务特点也不同,面向C端的业务,前些年因为年轻用户居多,产品设计人员偏年轻,在产品做主导的公司或创业型项目,可能要求一线技术人员也偏年轻,才能跟上产品的思维,“项目不在风口,立马就换一批业务,非常需要创新”。有互联网大厂就提出培养干部的“三板斧”,即强调心力、脑力、体力。但面向B端的业务,产品更注重稳定性,对产品的丰富性需求不强,就更侧重技术团队的能力。
陈方表示,大厂并不会特意淘汰岁数大的一线岁以上的员工上有老下有小,其体力和精力可能会有所下降,抗压能力也会差一些。
2020年9月,陈明进入当前就职的公司,从事技术架构师,这是他喜欢的工作,他认为代码和系统架构有其美好之处。已经38岁的他自称,“换工作比较慎重”。一年多以来,陈明在家远程办公,工作之外,还能兼顾家庭和孩子,目前的工作内容、强度与节奏,与他的状态很吻合。
曾经,在30岁出头时,陈明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,当时考虑的是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正盛,能学到更多技术,也能增强个人竞争力,但后来公司业务发展受限,他选择主动跳槽。
同在互联网行业,虽然并非研发人员,刘萌也不得不考虑新的职业方向。2022年4月,35岁的刘萌遭遇裁员,离开一家互联网大厂。此前刘萌在大厂做综合业务,入职时还负责管理团队,她在怀孕后职业发展受到影响。孩子逐渐成长,需要更多的陪伴时间。两年前刘萌开始思考职业转型问题。
协商离职敲定后,刘萌甚至有一点“轻松和解脱”。她此前的经历,使得她在大厂的职级和薪资都不错,但工作内容枯燥,也时常加班,这对她来说“并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”。
接受采访时,刘萌已经在家赋闲两周,还没想清楚下一步的方向。刘萌说,她或许还会选择大厂,看能否找到工作兴趣和成就感,也可能尝试做自媒体,时间自由地做点事情。受到收入多元论观念的影响,这几年刘萌也有副业,经营社群,卖母婴产品等,收入也够孩子日常开支。
在研究初期,夏冰青重点关注互联网从业者动态,但随着研究深入,她发现必须宏观地观察整个行业的变化。从2015年开始,夏冰青重点观察研究互联网产业的宏观变化。“那一年,正好是互联网产业出现高度集中化的发展态势,大厂纷纷加大并购与投资规模,从最初的内部研发转向并购、投资以及外包并行的模式。更多的互联网大厂选择‘购买’已经拥有固定用户群的产品,而非进行自我研发。”
在夏冰青看来,这一趋势导致一些大厂的工作内容开始变得愈加标准化、系统化和重复化。所以,在夏冰青的观察中,从业者在近几年越发体会到在大厂学不到太多技能,更多的是在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化生产。“自己扮演的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角色,这实际上也是‘大厂’这个词的由来与背后深意。”夏冰青说。
高强度加班、内卷严重,这些互联网从业者经常提到的问题,都应该拉长视线去解读。夏冰青表示,这和近些年互联网工作被切割得更为细化有关。从发展角度来说,一个产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,工作会变得更为标准化、工业化、系统化。“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进入的阶段是,很多大厂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产品和服务,大到新的产品开发,小到公司内部的人事服务等。这就导致大厂中的工作缺乏创新性。而对于进入大厂工作的人来说,很多人最初是抱有‘实现创意’的理想,这就使得这些人对于‘创新不足’或是‘无法体现价值’的工作方式抵触感更深。”
夏冰青认为,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断调整项目,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盈利。一旦发现所购买的产品/公司,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,就会快速拆分这些项目,进行所谓的“优化”。身在其中的从业者就会直观地感受到不断地被调整项目/小组,被间接或直接裁员,这也是互联网从业者高频高速流动的一个原因。
冉涛认为,从互联网1.0时代到2.0时代,从信息化到电子商务,随着技术进步,未来可能进入更具颠覆性的互联网3.0时代、4.0时代大厂中年人:重复劳动、缺乏,每次变革都带动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转向,对从业者的技术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。而这些年信息化建设的加速,企业数字化转型,带动各行各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增多。他观察到,35岁以上的程序员离开大厂后,通常有几条发展方向。比如,选择创业型公司做持股合伙人,进入国企做研发,自己创业或承接外包项目等。
陈方建议,职场人应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,才能更好地拥抱变化。陈方曾查阅过各个大厂负责人和高管的公开简历,“在这个充满想象的行业,没有一个人的路子和其他人一样,他们的成长路径包罗万象。个人也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厂里。”
根据2022年4月脉脉发布的数据,35岁以上的大厂离职员工中,有超过40%选择前景可期的中小企业,38.2%选择独立自主创业。
赋闲近半年,杨曦虽然洽谈过一些大厂的工作机会,但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短期内还是会坚持主营业务模式,所以他倾向于自己创业。
杨曦在继续研发基金大数据方面的产品。他表示,国内基金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,散户们需要这方面信息的整合。同时,他也明白,没有大平台的资源和支持,这项业务很难做成。
入职新公司不久,李铭更长远的想法也是创业。他说,不少程序员都心怀用科技推动社会变化的初衷,虽然现实是残酷的。
2015年左右,李铭从上家大厂辞职,放弃期权,自带几十万元的“干粮”,与一个同事共同研发一个互联网金融项目。“我之前任职的那家公司已经上市,虽然和基层从业者实际上没太大关系,但我觉得已经在一个成功上市公司待过一次,该去初创公司了,因此成为前10号员工。”
当时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李铭很快发现“上了”贼船,合伙的那个同事只想赚快钱,并没有按照创业蓝图做业务,也不想给大家分享收益。李铭又回到大厂尝试孵化创业项目,但后来也并不理想。
互联网行业的股权期权激励机制,能让员工实现或接近“财富自由”,这是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因素之一。对此,夏冰青表示,即便是对第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,持股背后都有很多代价,比如并不是人人都能持股,持股也不意味着一次性兑现,很多时候持股会成为人力与员工谈判的筹码等等。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招人,会给出一个package薪资(打包价),里面的股票事实上是由一部分工资转化的。对于员工来说,这里面有很多风险,比如公司股价下跌、股票兑现需要不同的服务年限等。随着互联网公司股票的下行趋势,尤其是这两年中概股的屡受重创,“使得一些从业者对于‘依赖股权/期权激励实现财富自由’的梦想变得渺茫”。据她观察,短期快速盈利的“逐利性”也迅速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中蔓延。
在暂离职场的“空窗期”,刘萌虽然还没有明确近期目标,但她发现自己挺开心的,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,能在温暖的春末夏初享受阳光,不像以前上下班总见不到太阳。在街上闲逛时,她有些恍然,“生活的状态有很多种,不一定非得在格子间里卷来卷去”。